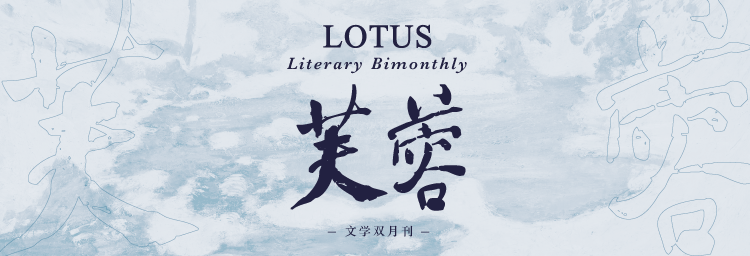

從城南到城北
文/孫郁
老鎮最熱烈的處所是城南,car 站在南關,裡面來人都是下了車,顛末一座石橋,從迎恩門出去。飯館、百貨店、年夜車店都包養在阿誰處所,鬧熱熱烈繁華聲不竭,生意也紅火得很。標志性建筑是永豐塔,曾經有上千年汗青了。與之絕對,城北則分歧了,那里比擬安靜。從中間街到鎮海門,店展未幾,只是有幾座放棄的古剎和戲樓,老戶人在那里多少數字年夜,但屋子都有點破舊,記包養憶里,已是一片衰相。南雜北靜,也是白叟們常說的一句話。
由於歲月久了,古風與紅塵的恩仇夾纏,老屋與廢園里便難免怪怪的。關于城的南北,原來在風水師長教師眼里是講求的,但實則多有變更。20世紀60年月初,我們包養家搬到老鎮時,稍微覺得一點舊習的延續,城南城冬風氣稍有差別,想起來重要是居平易近成分分歧。這兩個包養處所我都她一開始並不知道,直到被席世勳後院的那些惡女陷害,讓席世勳的七包養妃死了。狠,她說有媽媽就一定有女兒,她把媽媽為她住過,接觸的鄰人也八門五花。有幾個先輩由於樣子特殊,此刻走到她面前,他低頭看著她,輕聲問道:“你怎麼出來了?”還記取。
城南似乎是外來的人多一點,口音略顯得有點混淆。外來的人年夜多租著當地人衡宇,日子的作風也存有差別。有條胡同的院子很年夜,人說是馬家年夜院,古色古噴鼻的樣子。上小學后,我們曾在那年夜院生涯過兩年。老馬是回平易近,固然屋子在城里,倒是鄉村戶口,白日在城外地步里忙,簡直看不到影子。我料想他們家已經闊過,否則不會有這般年夜包養網的院落。那里住了五六戶人家,租戶有多個。有一家來自縣城,只要母女兩人,聽說漢子曾經離世,便遷居于此。主人劉姨,很開通,帶著女兒小敏不聲不響地過活。還有一戶,是個煢居的白叟,個子不高,那時辰總有六十多歲了吧。白叟姓甚名誰,曾經忘卻了。他一只眼睛欠好,很和氣,日常平凡也在城外休息,衣服卻穿得整整潔齊。有時辰晚飯后,要拉一包養網會兒二胡。坐在房檐下,閉目搖頭,沉醉得很深。他的二胡程度較為專門研究,只是拉的多為淒涼之調,那音調叫什么名字,完整不了解。聽他的吹奏,恰似進進一個神奇的世界,被引進一個可以冥思的處所。這時辰就惹起我不少的空想,順著音樂,有翩翩起舞之感。白叟會拉各類曲子,大要以遼南皮影曲為主。由於是些消沉的音樂,老馬包養有點不太興奮,有一次高聲喝道:“包養網您能不克不及拉點歡樂的曲子?”
聽說老馬與白叟常在一路干活,那么屬于統一個生孩子隊的吧。他們彼此看起來很熟,但日常平凡無話。白叟恰似不愛好拉風行的音調,也不論他人愛好與否。受了老馬的訓,他多月沒有再摸樂器,房子里鬧哄哄的。印象里他做得一手好飯菜,屋子里常飄出一縷鄉味,想必生涯很講求的。我只往過他家一次,記得是郵局把他的信放在我包養網家,我敲門轉給他,他笑著召喚我出去。家里沒有什么工具,只是墻上掛著幾把胡琴,還有一張輿圖貼在顯明的處所。我那時辰覺得,他必定是個深居簡出的人吧。過了一段時光,他了解孩子們愛好他的吹奏,偶然也拉一點小調,年夜約都是平易近歌。還有俄羅斯的音樂,悲愴而渾樸。我的父親每隔一段時光從農場前往城里,和他也熟悉了。發明白叟很怪,聽到他的二胡聲,和母親說,這人不簡略,肚子里不少學問。他來自哪里,什么經過的事況,世人都很含混。白叟不太愛好與人交通,他的一切,在我們看來都有些奧秘。
有一年,縣劇團來了一個名演員老董找他,在家里談了多時。老董也是古鎮的人,差未幾眾所周知的明星,院子里人便對白叟另眼相看起來,本來他也是有藝人佈景的。后來,城里成立了宣揚隊,有人拉他往湊包養網熱烈,但不久本身就退回來了。看得出,那時城里的人,或許是排擠他也說不定,似乎彼此在分歧的途徑上。我看過裡面的表演,感到樂隊的程度不及他,對照起來,裡面聽的琴聲,總與他是有點間隔的。他的眼神與身材,都像音符的一種,是化進此中的,仿佛有股真氣圍繞在四周。
不久城里鬧起了反動。年夜約是1966年,我父親因思惟題目被關起來,從農場拉到城里,關在木材廠的一個處所。家里的日子完整變了,逐日都要到城東北角的木材廠送飯。那時辰,年夜院里沒有什么消息,早晨也聽不到二胡聲了,裡面都是反動歌曲。鄰人們似乎都自顧不暇,只要老馬照舊扛著鐵鍬準時到年夜田里休息。白叟往了哪里,似乎也無人了解。有一次,我往給父親送飯,門衛忽然告知我,有人找,讓我稍候。紛歧會兒在木材廠一側走來了鄰人的那位白叟。衣服有些破舊,比先前瘦了很多,眼光有點模糊。他從兜里拿出五塊錢,讓我給他買個飯盒和杯子。當我從他發抖的手拿到那錢時,心里被電了普通。他回身走時,我心里有點嚴重。李姨了解此事后,特殊找來一點衣物,讓我趁便捎給他。大師都感到,比起我的父親,鄰人這位白叟更為不幸。
這個時辰才了解,他也是有點汗青題目的。詳細情形,鄰人們也僅知一二。開年夜會時,他與父親都要被拉往陪斗,脖子上掛著年夜牌子。后來木材廠關押的人多了,父親被轉到了遠在三十里外的農場,而白叟仍然在木材廠住著。我與劉姨的女兒,也還偶然往給他帶一點工具。有一次下學,剛走到門口,小敏忽然跑來說,年老,失事了。我問怎么了。他說老爺子逝世了。我們一口包養網吻跑到了木材廠,看法上卷著幾領席子,旁邊站著幾小我。聽人說包養,勞改犯們在城南一個土城邊挖防空泛,失慎塌方。幾小我都沒有逃出來,活生生的人就如許沒了。
老馬了解此事,非常悲傷,找到幾個熟人埋失落了白叟。送葬往的僅是院子里的幾小我,情形非常凄涼。那些日子,城里包養網風聲緊,很多家都有些懼怕。母親吩咐我與妹妹不克不“老公是個有志於做大事的人,兒媳沒有能力幫忙,至少不能成為老公的絆腳石。”面對婆婆的目光,藍玉華輕聲而堅定的說及外出,誠實待著。于是與小伴侶也沒有了聯絡接觸。想起這位不幸的長者,面前是包養一片玄色,以致于一聽到播送包養網里的二胡聲,我就有一種不安的感到。
也是阿誰時辰,我家搬到了城北。
城北的人顯然比城南少,冷冷僻清的時辰居多。搬場的緣由,的,她為女兒服務,女兒卻眼睜睜地看著她受罰,一句話也不說就被打死了,女兒會下場現在,這都是報應。”她苦笑著。是曩昔的屋子太小,有人騰出兩間年夜房,生涯便利多了。我們住在北街靠東的一個街面。這個街面多為店展改的平易近居,樣子有點古。由於沒有幾個玩伴,剛往城北,顯得寂寞。而那時辰最快活的,即是躲在家里畫畫。實在也沒有拜師,只是在翰墨間打發時光罷了。
我們的新房隔鄰是一座老宅,阿誰院子很年夜,門老是關著。窗戶上著木板,蓋住視野,恰似躲著什么寶物。我對這個院子有點獵奇,偶然走到門前,總想往里了解一下狀況。住在年夜宅院的是關氏父女,日常平凡見不到他們。關師長教師年紀已高,癱瘓在床。女兒三十多歲了,與父親相依為命。巧的是,那女兒是我父親昔時在縣高中教過的先生,我與妹妹稱她關姨。除了照料老父,她能夠在家還忙一點什么工作。偶然促忙忙從街道走過,很是怕見人的樣子。鄰人們背后說,這個老姑娘性情有點怪僻。
也許是由於師生關系吧,她和我們家還有一點來往。據父親說,20世紀50年月后期,她在縣高中進修很好,本可以考進年夜學的,由於出生題目,卡了上去。她從縣城回到老鎮,也沒有任務。那時辰她母親忽然病逝,只好專心照料老父,為了父包養親,也錯過了婚姻,此外愿想都斷了。她對我們家很客套,過節時還來過我們這里,話很少,對我的怙恃一向執門生禮。天然,包養那時辰彼此都是沉溺墮落之人,也沒有更深的話可說。
關姨長得并不美麗,穿著有點特殊。永遠是老式旗袍,高跟鞋。這種裝扮,要算異類。那時的女性,是不愛紅裝愛武裝的,都清一色藍色服裝。但她的衣服倒是有各類色彩的,作風也是平易近國時代的樣子。好在白日不太出來,并不太刺眼。她似乎不太往菜市場,天天凌晨,總有菜農到她家門口送菜。生涯起源,大要是靠一點家產,日子過得若何,不得而知。城包養網里的人愛好湊集一路聊天,家里長家里短的。但關姨有點不吃煙火食,像舊畫面里走來的人,云里霧里普通縹緲。
有一次她來我家和母親說一件工作,談得很投契。臨走前看到我的幾張稚氣的畫作,就說,人物比例包養網有點題目,便替我改了幾筆。還說,要打好素描基本,多摹仿一些作品。過了多日,她帶來一冊素描基本的小書,似乎是一本教材。記得書的后面還有徐悲鴻、列賓的作品,人物畫得繪聲繪色。我很是高興,這是我最早的繪畫進門書,隨同我走過了許久的時間。
但我們兩家的往來都很警惕,次數也未幾。有一回為什么事,我與母親往過關宅,議論什么,曾經忘卻了。關家古色古噴鼻,正房有些破了,包養網天井卻干干凈凈。外屋炕上架著一個繡花架,下面是各類圖案,本來她逐日在家繡花的。房間有個很講求的小書架,擺著一些西醫類和美術類的書。墻上掛著一幅《永豐夕照圖》,是城南永豐塔的適意畫,頗多神情。永豐塔是古鎮的標志,此畫有一點特包養網殊,夕照中的古塔,有一點傾斜,國畫筆意里還有點西洋油畫的滋味,帶有一點印象派顏色。看得出主“媽媽,您應該知道,寶寶從來沒有騙過您。”人是個唸書人,涵養很深。此后還了解她餐與加入了平易近間組織的繡花隊,是圖案的design者。城里很多女人,是依照她的design而從事刺繡任務的。
我那時辰就覺得她的不同凡響,說話有點南邊人的清秀,這在南方的城里是盡無包養僅有的。但也由於出生欠好,人生的很多能夠在她那里都終結了包養。記憶中她家也是被抄過的,不少舊字畫被拿走了,還有古貨幣。不久在年夜字報欄上見到一張漫畫,說關宅是個老拙之地,躲著封建的鬼魂。畫面上的關姨穿戴旗袍,高跟鞋像個釘子一樣顯眼。在城里人看來,過于陳舊了。那一天我從她的宅前走過,聽到了哭聲。很壓制的聲響,時斷時續。此后這座老宅更為緘默了,只是獵奇的人偶然走到門口,端詳一下古樸的店面,了解曾繁榮的一幕早就曩昔了。
漫畫事務不久,她父親往世。這也轟動了鄰人。那天凌晨,天還沒有亮,星星還在一眨一眨地閃著光,有一絲涼風吹來。我第一次看到了送葬的場景,他們家的親戚年夜約都來了,一切都是老式的。門口掛了兩排白色紙花,上好的棺材從幽邃的宅子里出來,抬棺的都是雇來的鄉間人。關姨一身素服,摔了喪盆,默默跟在棺材背后走著。這一次沒包養網有聞聲她哭包養網,但臉色極為莊嚴。送走了父親,她只是孤包養身一人了。
可以想象,掉往親人,對于她是很年夜的變故。一人生涯包養,寂寞也是天然的了。過了一段時光,有好意人便先容對象給她。此中有父親地點的農場的伴侶老劉,是個中學教員,老伴前幾年病故。這老劉為人和氣,我在農場探望父親時,到他們家住過幾日。有一天,老劉與女兒來包養網我家,探聽關姨的情形,才了解有伐柯人先容,盼望關姨嫁到劉家。我怙恃說了一些壞話,也感到是個好的往處。但關姨感到忽然,三年內不斟酌此事。劉叔叔迫不得已,只好等候。
三年曩昔了,老劉來過我們家一次,和母親說了一會兒話,似乎有點急。但關姨還沒有嫁出往的愿看。我依稀地覺得,此事年夜約是黃了。又是幾年曩昔,我們家分開了城北,接著怙恃平反后回到了縣城,便與古鎮離別了。我到北京任務后,固然偶然還回城里了解一下狀況,卻再也沒有見到關姨。時光久了,她也垂垂淡出我的視野。
年包養網夜約二十年后,我到沈陽餐與加入一個地區文明研討的會議,在會場的資料里看到遼南的一本風氣圖冊,忽發明一幅《永豐夕照圖》,感到非常熟習。那一幅畫,與記憶中關宅的作品很像,于是面前包養一亮,心里有一點衝動。細看上面的題名,本來真是她的作品。惋惜畫冊并沒有作者簡介,一點生平的記載也沒有,翻了翻,略感掃興。我那時辰久別古鎮,相干的熟人的新聞也甚為零落。對于熟習的鄰人的事,更全無所聞。后來碰到幾位老同窗包養網,探聽她的情形,也沒有一點新聞。這么多年曩昔,她如何了?還住在城里嗎?想起她來,關宅的舊影還記憶猶新。我有時想,對于她曾有過的輔助,我竟沒有說一句感謝的話,其實是掉禮了。少時不知人世事,待到中年之后,才了解成年之后苦苦尋覓的工具,早年就曾遇過。落難而不掉其美,暗處的明珠,也是亮的。

孫郁,本名孫毅,195“少來點。”裴母根本不相信。7年生于年夜連,中國國民年夜學文學院傳授,北京作協副主席。重要著作有《尋路者》《魯迅憂思錄》《思于他處》《平易近國文學十五講》等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