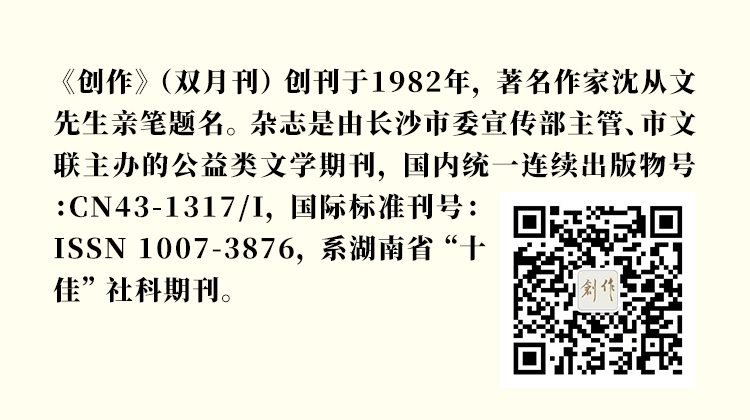——評湯紅輝詩集《月光流過人世》
文/陳啊妮
湯紅輝是行走中的詩人。他的詩歌是詳細的、具有地區性的,也是自力的、具有個別性的。他是善于在遼闊社會見尋覓鄉情,又能于鄉野發明世界的詩人,同時他也是今世包養價格語境下抒發天然幽古之情,并在城鄉分歧的生涯場景間不受拘束穿越的高手。《月光流過人世》這本詩集共四輯,有一百多首詩,真正的記載了他魂靈的觀光。他愛家鄉,因在異鄉對家鄉進一個步驟地所以,財富不是問題,品格更重要。女兒的讀書真的比她還透徹,真為當媽的感到羞恥。辨識,而在異鄉傾瀉了情義——也許由于消息任務者的成分屬性,家鄉與異鄉的界線對詩人來說是含混的,如《華盛頓的第一場雪》《在洞庭湖碰見家鄉》等詩就表現了這一點。體識到湯紅輝詩歌的這一特色,有利于更深入地體察他詩歌的魂靈氣韻。
他不是于密包養站長屋中“制造”詩歌的人,而是于行走中創作。一首詩與他的“相逢”,在于他的習氣性留心和察看,但不成否定也有那種難以名狀的偶爾,撞進他的心間。詩人與“存在”的偶遇,如芳華期男女的一見鐘情,沒有更多的事理可講,詩性或許所謂的神性,等是等不來的,找也是找不到的,在于“機緣”。如有緣,甩也甩不失落。但假如湯紅輝是沒有預備的詩人,只是恪失職守的記者或不雅光客,沒有一顆詩心,就難以發明只要懷揣詩心的人才幹發明的工具,也難以寫出只要詩才幹承載的說話。消息業包含萬象,且年夜大都情形下,從業者更應以感性和嚴謹立品,所以詩人這種“一路沉吟”是包養留言板無限度的,是詩人在特定剎時的認識旋飛或推翻,一種與在心坎沉潛許久的性命不雅念的碰撞或對接。
詩人在《人世聽雪》和《異鄉家鄉》中告知我們的有經歷現實,更多的是超驗的“存在”—包養app—詩人魂靈世界的浮現。湯紅輝詩歌的價值,更多在于后者,對所察看事物的超出性的審美想象。他既忠誠展示了世界本態,又真摯地告訴我們另一種狀況;實際的時光和由詩人體驗的“詩性時光”,兩者融合,但又彼此自力。如《默坐塔克西拉古城》中的“游人離往/神鳥低飛/在唐僧谷門前閉目默坐能聞聲梵音縹緲/我是一個遲到的沙彌”,再如《華盛頓的國度廣場有個馬丁·路德·金雕像》中的“他的身材里流淌著湘人的血液/每次顛末/我都仿佛聽到他用湖南邊言向我們打著召喚”,都很好地表現了這一點。詩人完整包養妹沒懷孕在異域的生疏感,他似乎不愿提醒國際外人文的異同,在他這里,家鄉無處不在,也無時不在,可以隨時發明湘人的骨肉和睦韻。
《人世值得》這首詩甚至可以被以為是對詩人心坎最隱秘的部門的奧妙提醒,也是他的人生或命運包養站長。人世在詩里已然同化或稀釋為自然或具有神性的“小妖”“溪水”“石頭”“陽光”,包養網這似乎是與日常的世俗販子“平行”的另一小我間。這首詩是自我證實,詩物證明本身是一個癡迷于人世的人,一個在包養陽光下奔走、汗流浹背、欲看滿溢的人,更是孤單而安閒的人,正如他在詩中寫下的“人世值得/還有百年的時間足夠浪費/只是端起桃花酒樽能與誰對飲/就像此刻/不知該把信息告知誰”。另一首《此刻我正走在紅塵的陌頭》,也是這種本真經歷與詩歌說話彼此發明的詩。這首詩濃郁的“孤單感”浮現的是詩人心坎的深度,具有一種幽秘又不受拘束的放飛感,它是詩人從實際紅塵橫曳出的虛幻,更是詩人對說話纖敏獨到的觸撫,從“此刻我正晚回走在紅塵的陌頭/夜色如水/沒有人看到它們的影子在我身上交錯”如許的詩句可見一斑。人世也好,紅塵也罷,湯紅輝用精簡的意象,確立了“我”的位也有蘭家一半的血統,娘家姓氏。”置和立場,更正確地說,確立的是“我”作為詩人的血性和骨力、情愫和睦質。
《過鹿坪》和《天門山》這兩首詩都是詩人在旅行包養網心得過程中的霎時之悟見,從中可以一窺湯紅輝對“氣象詩”的寫作立場,即詩中的滄桑況味、內植的悲憫與柔嫩,這是從“見山不是山”向“見山是山”的有意識的天然改變。湯紅輝對風景的熟悉,以古典美的視覺化漢語浮現,而不是故作智性或哲學化,對景不雅作過多釋解,讓人認識到察看者看到的不是表象,而是難以揣度的“實質”。在此,詩人更情愿帶著感情,把他所見“說明白”——他“看”到什么就說什么(當然包含他心坎“看”到的),這么做有利于讀者留意詩歌說話的騰躍和游走,聚焦說話自己的發育與發展,唯有這般,一首古代詩才幹如古詩那般,煥發漢語自己潛伏的光焰,使得文字本身的奧妙,尤其是那種蒼莽和溫婉得以表現。所以總體上我以為這兩首詩寫得有聰明、成熟,沒有涓滴的矯情、虛偽和造作。好比“必定有一只鹿穿過白日清風/農夫正揮鋤鏟土撒下第一粒種子/小孩田野中追逐遊玩竹馬青梅/必定有一只鹿穿過如水月光/女人正躺在漢子臂膀閉眼撒嬌/孩童磨牙夢話/鹿過/幾朵梅花飄落”(《過鹿坪》),又如“天門洞是天眼/上蒼有慈悲心腸/對人間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”(《天門山》)等詩句,既不乏古典文學和傳統文明的浸潤,又有厚重而深闊的古代性。《在黑山頭尋撿石頭》《在呼倫貝爾草原》《呼倫貝爾的色彩》等寫草原的詩,充足施展了漢語的視覺化魅力,告竣了聲響化後果,有草原上的雄姿英才之色,又有琴弦婉轉之音。不成疏忽的是,湯紅輝很器重寫景詩在視覺轉達上的正確性包養合約,這種正確是詩性表達的抵達和糾偏,如“當夜幕像法衣籠罩草原/星斗裝點其上/馬頭琴開端唱響如泣如訴的長調”“只要這個時辰,才點染了那么一抹鵝黃”(《呼倫貝爾的色彩》)等詩句就表現了這一點。
親情詩在這本詩集里占有相當的分量,也是我重點瀏覽的部門。由於親情詩人人能寫,但寫的具有震動人心的氣力,就很不不難了。湯紅輝顯然是采用純潔拙樸的說話戰略,盡無抽象的意象,但這種說短期包養話寫出來的“親情詩”反而具有告終實的氣力。感情的過火宣泄現實上是一種自戀,如艾略特所言,必需“自我之迴避”,把“我”純潔的囉唆往除失落。我們來讀一讀《病房里的父親就像我八歲的女兒》:
包養七旬老父親從鄉間打來德律風
說腰痛得直不起來
我設定堂弟開車把他送進病院
忙完手頭任務已是五天后
我買了一些吃的趕到病院
父親坐在病床上
把各類醫藥單逐一攤出來
絮絮不休說給我聽
那一刻
感到他就像我八歲的女兒
見到出差很久才回家的我
這首詩所陳說的就是現實產生的“舉措”“經過歷程”或“成果”,詩人本身沒有抒懷,而讀者的感觸感染完整來自現實,而非詩人的感化。親情詩自然是用來激動人的,讓人共情,而不是進修某包養網VIP種邏輯或常識,但這份激動盡不克不及是“二手貨”。湯紅輝深諳此道,他的良多親情詩,無論是寫雙親,仍是姐姐或孩子的,都苦守了樸素之道,他很是甦醒地熟悉到:最值得同情的,是詩中的父親或母親,而不包養app是處于哀傷中的詩人。親情詩中的“我”,最好是一個沉著的傍觀者、記載員和攝像師。當然不克不及完整防止自我感觸感染的抒發,但最好別說出來,經由過程“行”而非“言”表達。如《下雨了》這首詩,說的也包養行情是平凡的一個早晨,包養網一個雨夜,詩人和一個叫“瑟瑟”的兄弟用微信交通的情形,“平庸”如拉家常,那“衝擊人”的尾句,“抑或是回到洞庭湖畔寫詩/寫到最后/總寫出淚來”,是天然而然說出來的。《離家》論述的,也是再平凡不外的情形,但最后一段的寫實讓人一顫:“分歧的是/小女翻開車窗/一個勁向爺爺奶奶說再會”——這是一切人都經過的事況過的,但詩人匠心獨運的文字,顯示出奇效。《在東風里覺醒的姐姐》非常動人,“姐姐”能夠是全國除了“母親”之外最暖和的名字了,“曾屢次包養網與你遠遠相見/卻不曾喊你一聲姐姐”。《三更夢醒》固然寫的不是現實情形,是個夢,但也是樸素逼應的恩情。”真包養網的夢,詩人漠然地論述這個夢,越鎮靜安靜越讓讀者肉痛。
城市與村落有著一種糾纏的關系,尤其是從小在村落長年夜、后來在城里生涯的人,對過往的阿誰保存周遭的狀況情感復雜。兒時村落的生涯經過的事況如包養意思胎記(仍是第一次看到詩人將鄉土稱為“胞衣地”),對本身的影響是畢生的,但跟著歲月流轉,人在城里生涯久了,尤其是滿世界游走后,對村落的印象會變淡,村落或突變為符號和概念,不再詳細,在心目中不再包養網鮮亮。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對村落的記憶與天然風景、與靠天吃飯、與兒時的自由自在,有脫不開的關系。沒有人想回到曩昔,想歸去的只是心靈——在那樣一個世道,赤貧反而映托了質樸和天然,或作為生物的包養網極簡的知足和快活,還有怙恃親及更老一輩的人,對后代“純棉質”的希冀和庇護。湯紅輝無疑表達了對家鄉深切的情感,但不是空包養網洞地抒發,他用精密的點滴情節支持了鄉愁。《回到村落》很正確地描寫了回到鄉下后,詩人再不成能一身雨水或一頭灰地盤休息,“光腳在土壤上奔馳包養甜心網”,“蓑衣竹笠掛在墻上/我們在一杯清茶里操琴/或許捧出版本/面臨窗臺上的噴鼻蘭/漸漸把日子翻開”,這是對實際的寫照,字里行間吐露出一種輕松與浪漫。我以為,湯紅輝對城市的熟悉,跨越了對村落的熟悉,村落對他來說只是兒時的幻包養網想或記憶,但城市生涯是黑色的、幻化的,是他作為通俗鄉村人的尋求,但在城市生涯久了,又會有競爭和成長帶來的壓力,因此時常悼念起村落。詩人在《做一對城市里的鴿子》中寫下“假如可以/仍是做一對鴿子吧/可以在城市飛翔甜心寶貝包養網/也可在城市和村落之間隨風棲息”,但這只是一種企看罷了。《留念日》是詩人在城市找到了一個新的詩性的“安身”,或于喧嘩中純然的包養情婦捕捉,正如他寫的“一切的許諾都到哪里往了/回一回頭/胸口煩悶/有得出結論的那一刻,裴毅不由愣了一下,然後苦笑道。點痛/站在高樓伸出手往/好像想握住一縷風”。即使這般,詩人總仍是會在不經意間憶起童年的鄉下故事,如包養網車馬費在《我看世界的目光加倍佛性》中寫護士給本身打針時,“想起小時辰在鄉間宰殺田雞”,及至《在天安門對面穿戴三角褲衩四處觀望》這首詩,詩人的風趣和俏皮更顯示了他心坎抹不往的童年,“急忙中穿好衣服/想想也沒有什么/站在母切身邊撒潑/我怕誰”如許的詩句恰是這一點的寫照。我要說的是,村落和城市對湯紅輝來說是沒有界線的,他對城市有感性、極具聰明的懂得,對復雜的人人間具有自我的評判,并因奔忙于全國而擁有豐盛的經歷,但他心坎一直有家鄉,有童年,它們是理性、質樸的,村落和城市在詩人的詩歌輿圖上包養網,沒有鴻溝,或鴻溝含混,就像他在《我是一條狗》中寫的“但我仍將叫下往/直到滿村的人/學會用狗語/往交通戀愛”。
這么說,他生涯的城市也是他心坎包養網車馬費的某村,全世界即“滿村”。
(原載于2023年第6期《創作》)

陳啊妮,陜西文學研討所特聘研討員。作品在《詩刊》《星星》《詩潮》《詩歌月刊》《詩林》張。《延河》等百余家期刊頒發并進選多包養管道部選本。評論進圍第六屆“詩摸索·中國詩歌發明獎”。著有《與親書》(合集)。